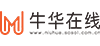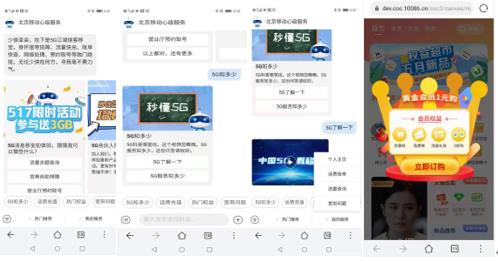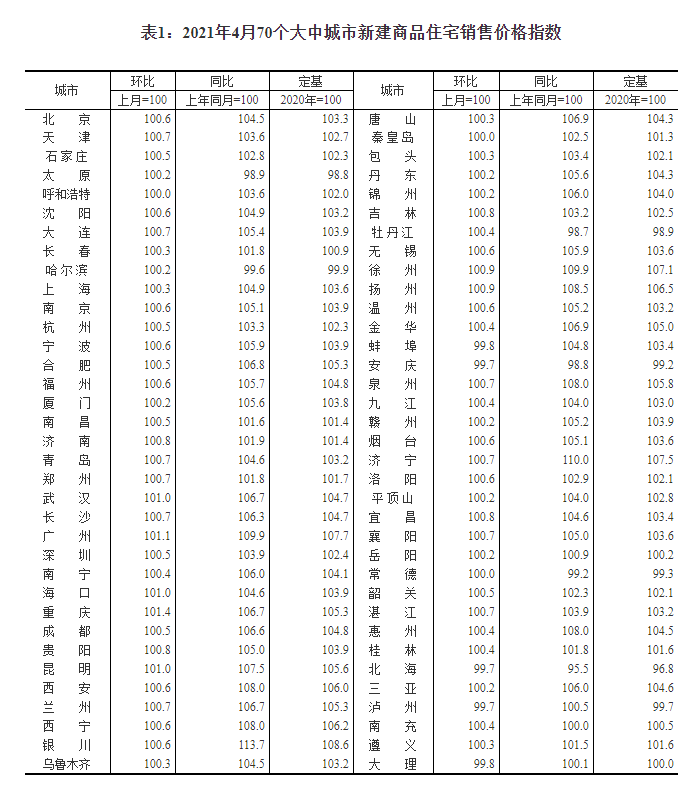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文 | 深瞳音乐,作者 | 河马君、楚青舟
最近,仿佛整个网络都闻到一股《乌梅子酱》的甜香。
李荣浩去年12月发布的这首歌曲同时霸榜QQ音乐、网易云音乐,在它爆红的原生地抖音上,更刷出超15亿播放。
“抖音神曲”并不新鲜,《乌梅子酱》能激起如此热烈讨论,更多因为这是李荣浩;以及丁太升等的批评,认为这首歌有一种鸡贼的俗气,李荣浩失去的心气,过分讨好下沉市场。
《乌梅子酱》真是俗不可耐吗?平心而论它算是一首无功无过的小甜歌,短视频批量制造过的众多神曲中,甚至算得上良品。
不过本文也无意花太多笔墨讨论歌曲本身。作为音乐产业观察者,我们真正关心的,是“《乌梅子酱》引起业内如此热烈讨论”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
丁太升们的愤怒,更多是来自于某种纵向对比,他们表面上叹息的是“从前的李荣浩”,真正怀念其实是“过去的乐坛”。这个故事,要从“很久以前”开始说起……
丁太升批评李荣浩,为什么“小镇青年”背锅?
丁太升说李荣浩作品失去了早期的诚恳,在投机,“投谁的机呢?小镇青年、初中毕业的文艺骨干”……
很有意思的问题是:喷李荣浩就说李荣浩嘛,小镇青年做错了什么呢?
或许,问题并不在于“小镇”与“城市”的对立,而是:“神曲”与“乐坛”的冲突,源头在小镇里。
今天的我们,已经习惯于将“神曲”和“抖音”绑定起来,以至许多年轻的朋友没有意识到一件事:神曲并不是短视频时代才有的新物种。
早在智能手机还没普及的2000年代初,就有依托手机彩铃和街边小店音响火起来的《老鼠爱大米》《香水有毒》《两只蝴蝶》等传唱度超高,但旋律简单、歌词浅俗的流行作品。
当时的专业音乐人们时不时也会哂笑一下“街歌”,却很少会像丁太升批评李荣浩一样,为反神曲“上那么多价值”。
那是华语乐坛黄金时代的末段,流行歌手们还能经常做出销量百万的“白金唱片”,唱片公司牢牢把控着上下游,再加上数字音乐刚刚兴起(国内第一个音乐网站九天音乐网上线于1999年),带来更多的期待:音乐市场的未来大有可为。
所以当时,街歌、神曲这些属于“下沉”市场的东西,都是不放在乐评人眼里的。
大陆本土音乐在商业上欠发达,导致整个流行音乐界的信息渠道是“自上而下”的,由欧美到日韩,由日韩而港台,再进入内地——无论是叶倩文邓丽君还是梅艳芳张学友,对内地音乐市场都属于降维打击,大发行商想要谁红,影视演员多栖也能红;想要谁糊,一个冷藏可以废掉专业歌手半生努力。各大排行榜也都还很有公信力……
换句话说,当年的流行趋势从来不会逆着音乐人的意思走。
而小镇,可能是那个年代音乐世界唯一的反叛者——流行音乐“王权不下县”,街头的小店店主并不按照CCTV、MTV的榜单来选他录音机里的歌,就像中国数千个广场上的大爷大妈们只等凤凰传奇和《小苹果》,绝不会看一眼列侬或者小红莓,因为下沉市场有自己的逻辑。
不过当时的音乐从业者们并不太在意这个问题,因为这些“俗不可耐”的歌也就是个乐子,它不会抢走利益。
回头看来,分外有趣,由街边小店的喇叭和广场上的收音机来做末端触达,所以“下沉市场”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小镇和乡村在音乐选择上声量很小,大众传唱的依然是唱片里的、晚会上的那些歌。
“小镇”的话语权增加,经历了一个量变慢慢到达质变的过程,更关键的变化,出现在抖音这样日活超8亿的短视频怪物身上。
以《乌梅子酱》为例,哪怕是头部音乐平台力推,带来的传播度恐怕也不能与抖音快手相比——抖快的底层逻辑是“掠夺”所有碎片娱乐时间,最终形成“视听垄断”。这点我想不必再多说。
音乐的生产—消费模型于是发生了一个巨大变化。音乐的传播完成了“去中心化”,脱离了上游的掌控。
《海藻海藻》《少年》《惊雷》《你的答案》《我们不一样》《桥边姑娘》……这些歌曲占据传播金字塔的顶端,让音乐人群体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境地,他们既不是真正阳春白雪的学院派,也不再是“流行”的主流,无论愿不愿意,整个音乐圈都需要调整心态来适应这个最大的现实。
丁太升话语中莫名的小镇青年论,仔细想想,其实是音乐人刻板印象的一部分,是对下沉平台的用户画像。丁太升们为什么敌视“小镇”?小镇是一种象征,打破了固有的传播模式,窃夺了流行音乐的话语权,在传播关系中处于强势地位。其实小镇一直都在那里,只是短视频怪物以超高效率不断放大传播指数,让小镇变成了某种威胁。
失去“金标准”,音乐还有好坏之分吗?
总有人说,如今是华语音乐的“末法时代”,说法夸张,却也有形象之处。随着“传唱度”这个金标准日渐失效,要以什么标准来分别好坏呢?商业和饭圈模式的加持下,榜单已不再具有参考价值。
“群众的眼睛”失去了雪亮的光彩,而小圈子的相互吹捧也令人厌烦,流行音乐似乎进入了一个没有标准的时代——李荣浩就是这么说的,“音乐没有好坏之分,只有你喜欢和你不喜欢”。
我认为,丁太升们对李荣浩的强烈意见也和这个表态有关,作为原有音乐生产体系培养的优秀音乐人,话语唱作人的“脸面”,你李荣浩不但主动下沉去“学猫叫”,搞“抖化”创作,竟然还要从理论上确认它合理,这不但是“叛徒”,而且丢失了音乐人底线。
说李荣浩“鸡贼”是成立的。音乐当然有好坏之分,专业水准与真挚情感,这都是“音乐人”这个身份存在的基础。李荣浩的言论与创作中,确实都能看到“主动下沉”,讨好流量主体的倾向。
李荣浩2018年的单曲《贝贝》,是一首只有4秒的话题性神曲,2020年的九字新歌《要我怎么办》,全部歌词只有“呵呵呵呵 我要怎么办”“哈哈哈哈 要我怎么办”。
就这2首歌而言,与其说是优秀的音乐作品,不如说是优秀的广告作品。
这未必全然是摆烂,但作为最优秀也最知名的华语创作人之一,受众和同行对他有更高的期待和更严厉的批评,这也合情合理。
流行音乐诚然需要大众的理解,但抖音等怪物的参与,明显也异化了传播。只要几个特定的和弦,就可以反复“洗脑”,成为“神曲”以后自然有人持币数百万要求商业合作——在这样的循环里,歌曲严重同质化、模式化。
哪怕周杰伦这样的天王,20年最火的《莫吉托》,其“传唱度”是否也和它的“抖化”有一些关系呢?
传统意义的流行音乐,失去了触达最广大受众的渠道——这也是整个音乐行业“不行了”的底层逻辑,当传唱性这个金标准失去,迷茫是必然的。
可话说回来,丁太升自己对《乌梅子酱》的评价方式也明显是设计过的。矛头直指“小镇青年、低学历打工人”刻意挑动争论,也充满了刻板印象。作为一名处处DISS抖化的专业乐评人,吃的却是抖化的流量,营销方式却也是依托于抖化传播环境的,这不讽刺么?
再者说,丁太升也实在算不上“小镇”的反面,真要论出身,他自己难道不是来自小镇,并且在小镇上有了自己关于音乐的想法和观点么?一位知名中专毕业生到处说人“没文化”,在音乐标准上搞“出身论”,这本来也很不合适。
音乐有好坏之分,不代表“音乐迷”的审美一定就高于“打工人”,好音乐的标准可以讨论,不能前定。
华语乐坛,还能“选李白”吗?
最后我想聊聊,音乐人究竟该不该害怕失去点赞——这实际上也是丁太升设计的话术,专门为了激起一部分受众的愤怒。
我认为,让听众(不仅仅是歌迷)听懂,是流行音乐人天然的义务,只为悦己而创作的音乐,其实都没必要进入流行工业生产体系中,要听众掏钱的东西,当然要以听众喜爱为标准。
只是“抖快”当道的模式下,许多业内人士和歌迷都有一个意见,认为现在的裂变传播“不是自然形成的”,视频创作者选择BGM一般都从众,也并不会细心判别音乐的好坏,使头部流量无限放大。
而短视频中的音乐,不再是“主材”,而是作为“辅材”存在,无疑也突出了音乐的工具性,消解了音乐创作自主性。这是专业音乐人和乐迷绝不可能接受的。
这种情况下,音乐人看待“点赞”其实该是两分的,广义的点赞是来自听众的肯定,依然是很重要的;狭义的“点赞”也就是某个APP上的按键,则不应该过分影响音乐创作。
白居易写诗追求“老妪能解”,这肯定是对的,可说到头,白居易也并不是靠老妪的指点来写诗。更何况,李荣浩的初心,难道不是“选李白”吗?至少这是他自己曾经的表述。“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那个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自言臣是酒中仙”那个李白……
《乌梅子酱》的味道或许并不坏,就是离李白太远了,更像是始终萦绕着“我认真学习了世俗眼光 世俗到天亮”的背景音。整个圈子也正需要安静思考,音乐的标准和创作的导向问题。
“雅”与“俗”并非势不两立,音乐审美更应该是自由的,流行音乐或许在等待一批变革者,重新找到专业与传播之间的平衡点,就像马三立侯宝林将天桥的相声艺术带上大舞台一样。
只是,李荣浩开始“学猫叫”的时候,他还能选李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