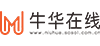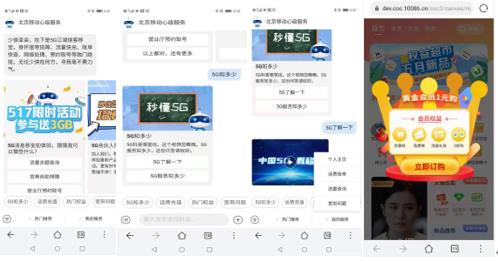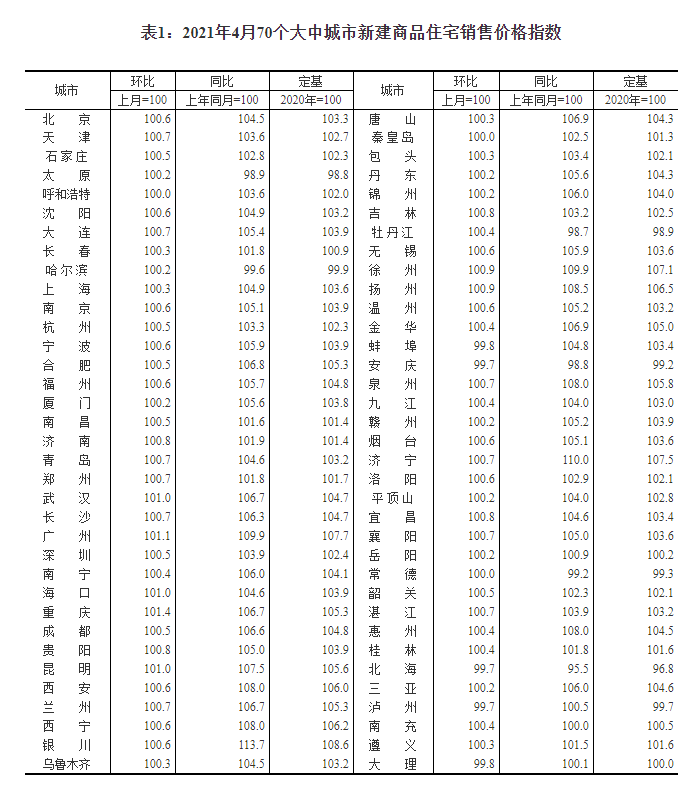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 | 五环外OUTSIDE,作者 | 刘奕然,编辑 | 车卯卯
你有勇气重头再来吗?
李鹏到了年尾,最害怕的事就是回东北老家过年。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回老家,就意味着要和亲戚朋友交换近况和寒暄。但如果别人真的问起“最近在北京忙啥呢?”自己还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尤其作为一个刚刚失业的北漂。
李鹏思来想去还是坐上了返乡列车,回家两天后才发现,很多亲戚都早在9月份去了海南。有条件的东北人都已提早过上了一种迁徙生活,今年老家只剩他和爸爸妈妈。
一家三口挤在两代户的小方厅里看电视包饺子,每临近年节,东北地方台总会循环播放历年春晚小品合集,李鹏浸在过年气氛里,庆幸自己最终选择回家。
直到电视屏幕里黄宏出场,一句“工人要为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戳破了李鹏的新年。
父亲摸起遥控器换了两个台,长长叹气,对于一个下岗二十多年的老工人来说,这句台词总是会触发一些遥远的伤痛,新年就此开始泄气。
李鹏也努力压下自己胸口的那声叹息,成长在一个被下岗潮冷水浸透的家庭中,让他无论如何都说不出自己已经失业的消息。
90年代末的下岗潮,是东北工人的至暗时刻,千万人集体失业,几代东北人从那时候开始,从骨子里惧怕朝不保夕。
东北下岗二代,持续半生的中年危机
王东从小最害怕的事,就是被人说他像他爸爸。
一个被迫下岗的东北中年男性,每天在家包揽家务、买菜做饭、洗洗涮涮,被媳妇挤兑不敢大声吭气。打王东记事起,他爸就是这个样子,半生渡不过去的中年危机,空闲时间全部留给喝酒和看电视。
二十来年父子关系一直很微妙,从小别人说“东东真像他爸爸”的时候他总要皱眉,成长过程中他始终不能理解,出去找份工作这件事能有多难。
从他上大学后就没怎么回过家,他实在不爱回那个只有5层高的单位家属楼,家里没人说话的时候总有听不见的叹息声,实在让人压抑。
所以打毕业起王东就打定主意不回老家,在上海工作多年,起起伏伏都见招拆招,直到2021年赶上公司裁员。
他所在的整个小组都因为“绩效考核不达标”的原因被全体砍掉,赔偿来来回回也没谈妥,29岁的人生在反复仲裁中被磨没了精气神。
根据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数据,2021年截至3季度末,上海市累计领取失业保险65.7万人。
王东在失业后很长之间内,每月都在靠着这一千多元度日。
2021年内领取失业保险的人员成倍攀升
临近年尾,投出的简历都打了水漂。很多职位在这一年中合并,需要能耐高的干不了,不需要能耐的看不上,生活在一次次眼高手低中卡顿,唯一变化的只有不断减少的存款。
王东想不如趁着机票还便宜,退掉房子回趟老家,利用过年时期看看工作、整理整理简历,存款正好能支撑到年后继续奔沪。面对家里,王东只和家里人说工作变动,年后再回去工作就行。
东北的冬天极度寒冷,回家的时候老家已经供暖,自己过去的房间已经被改成杂货间,床和书桌早早就被卖出。
他只能睡在客厅的沙发上,面朝暖气,他觉得自己可以一直这样冬眠下去。
全家人照样挤在老家属区的80平两室一厅里,妈妈退休后又在本地医院找了份工作,早晚倒班,爸爸依旧每天在家洗洗涮涮买菜做饭。
失业两个月后,王东达到崩溃的巅峰,冬天大雪封门,沙发就是他的起居室,每天一面躺着他,另一面坐着看电视的王东爸爸。
母亲每天倒班回家看到的就是这副样子,东北强势女性拥有压倒性的家庭地位,冷嘲热讽说“家里又来了一位大堂经理。”
家里多数时间只有爷俩独处,一人一杯白酒相顾无言
王东无能为力,还有半个月就过元旦,现在并不是离开家的最好时机。
按东北老家的年龄计算公式,周岁29相当于孩子应该三岁,而自己没女友、没工作,只有极少的存款和失业保险金。
投递出去的简历也始终了无音讯,妈妈勒令他找个工作先干着,总比在家待着强,别像你爸。
王东有点开始向生活妥协,看了一圈以后才发现,家附近能找到的工作没有双休,没有五险一金,算下来还不如领失业保险划算,为了不让妈妈过于不满,开始主动揽起家务早起做饭,以及尽可能避免待在家。
一个年轻人,突然被抽走了精气神,沉浸在眼高手低的困局中,每日只能寄托于表象的忙碌,执着于洗洗涮涮。
至此,他终于开始理解父亲,并开始承认自己确实很像父亲。
春节过去,东北四季分明,时间很快过去。王东在家失业一年整,好时机似乎永远降临不到他头上。
家属院老小区,成了他和父亲无法逃离的地方
赶上母亲上夜班,家里只有爷俩,王东给父亲倒上散装白酒,说自己过阵准备重新出发,压给父亲五千块钱。
父亲喝了酒难得话多,说起没下岗前自己最喜欢骑车、游泳和去火车站旁边的剧院,下岗是个记录时间的节点,从那之后人生似乎没什么值得提起的事情。
末了对王东说:“东东,你还想出去就去,能离开家是好事,你比你爸有出息。”
王东低头,眼泪落进酒杯里。
双减下的下岗二代:妥协、回归
早上朱姗姗还在和主管核对当周的课程表,晚上就收到了公司的破产通知。
之前早就听说过要“双减”,稳定军心的会议开了一轮又一轮。分区校长对他们说放心,价值万亿的校外培训市场怎么可能说没就没,安心上课,学校和家长都需要你们这些老师。
然而朱姗姗在收到企业破产通知时,还欠了3个月的工资没发,同事拉她进新群研究下一步该怎么办,有人在群里发了张截图,是分区校长的朋友圈,上面写着“十年青春给了谁。”
然而想要维权的不只老师,还有在学校充值了大量课时的家长。在一线城市,随便冲个半年的课就要12万,双减刀落,一切都打了水漂。
一个外培老师的平均工资在1.2-1.5万,旺季有人能拿到3万,链条突然中断,背负房贷和家庭的老师都不知如何是好。
朱姗姗四处投递简历,彼时能拿到的最好条件只有底薪4000。打听一圈才知道,有的老师被家长挖走当1对1家教,家长都不愿更换老师,收入甚至比过往更可观。
往常一天中最忙的时段,在最后一天灯都没能开全
有的老师能为自己找到出路,而朱姗姗只有傻眼。
原本打算接受那份工作的她开始犹豫,想打给家里听听建议。在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她的全家,都在东北下岗潮中陆续下岗。1997~1998年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黑龙江省有147.5万国有企业工人下岗。
先是大舅,后是二舅,接下来是老叔和爸爸妈妈,他们都属于一个厂区,草草用几万块钱,买断了后面的几十年。
童年时期的姗姗不明白具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买断”意味着有钱拿,亲戚朋友都住在同一栋楼,买断后就会都聚在奶奶家吃饭,有人买断的日子,就意味当天家里回做些好吃的。
她曾经在饭桌上说了句“我长大也想买断”后惹来母亲的一巴掌,那时她从没注意过,第二天家里就会增加一位不用上班的成员。
失业触及了她的童年创伤后遗症,电话接通绕来绕去不知道怎么张口。
从午饭吃的什么问到最近身体怎么样,爸爸早就听出另一面女儿的状况不大对,一一回答完毕问她“你最近怎么样?工作顺利吗?”
朱姗姗没由来的开始鼻酸,待着哭腔回答“我刚刚失业”,对面问为什么啊?你是辞职了还是被炒了?
朱姗姗回答“都不是,是我的行业整个全没了。”
说完俩人对着电话反而笑起来,爸妈都笑她太惨了,平头百姓谁也没能预料到的事儿居然能砸到你头上,没事儿,谁也不赖。
朱父在20年前遭遇过的中年危机,时隔二十多年同样发生在了他的女儿身上。
早年下岗员工凭着手艺试图再就业,如今也套用在朱姗姗身上
善于苦中作乐,是东北人民身上最为显著的性格特点。
“乐也是一天,不乐也是一天,那不乐多冤呐?”人们信奉这条生活定律对世界调侃嘲讽,即便苦难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下岗潮后两大对东北人伤口撒盐巨作,分别是黄宏的小品和刘欢的《从头再来》,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从头再来的机会和运气。
但朱姗姗一家都坚信,人只要活着就始终有重头再来的资本,02年开始全家凑集买断的钱,从练摊卖菜到开上小饭馆,有过受冻的冬天,看过亲戚脸色借钱。
中间不是一帆风顺,好歹风风雨雨多年都撑了下来。爸妈告诉朱姗姗经验之谈:保持心气,不怕挫折,凡事多看开,能不能站起来全靠自己。
朱姗姗挂断电话抹干净眼泪,准备去学校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很多拖欠薪水的同事准备把能拿的走拿走,同事拿起过去办公桌前的招财猫问她要不要拿走,朱姗姗说“不了,这招来得财赚得太晦气”,同事们集体发笑。
另外一件没人拿走的东西是办公室里的锦旗
姗姗手头还有些存款,自己当过老师又头脑灵活,总能找到新工作。
爸妈告诉她就是找不到也没关系,数学老师到小饭馆当个收银还是绰绰有余,没什么门槛,只要她会按计算器。
不甘心的下岗二代:逃离这片土地
“家里不需要你赚什么钱,只要你在身边就行。”宋柯妈妈给她打了无数次电话,每次核心概念都脱离不开这句话。
宋柯毕业后始终在各个城市中过着一种游离生活。工作以来无论在哪工资都没高过6000,她也不是很在乎这个,27岁在外面还好,放到东北未婚群体中就是黄土已经埋到脖子。
家里虽然顺应着下岗潮全部赋闲,但她从没过过一天苦日子,以及有过任何危机感和心理创伤。
在2000-2005东北经济极速衰退的年份中,大量的人没有医疗、养老和经济补偿。宋柯的父亲虽然下岗,但有个争气的哥哥,从下岗开始就跟着一起包工程抱大腿。在极不景气的年份中,全家还一起去过香港。
宋柯妈妈总说这一家始终风调雨顺,只有在她身上栽过跟头,常年游离在外地、频繁失业、大龄单身,用家里的钱租房,刷家里的卡。每个月贴在她身上的钱是东北本地退休金的三倍。
全家除了宋柯人人都很焦虑,工作倒是其次,家里不缺这点钱。缺的是社会地位和一个“正经工作”。
同时,她的终身大事是全家的共同目标,无论如何也要团结一心消灭掉,在家人眼中,女孩的价值在随着年龄增长和逐渐贬值。
实现这个计划的第一步,就是让宋柯从杭州回家。
上一份工作并算不上辞职,更像是长期考勤不达标的被迫失业,躺在出租屋几个月,接到家里的电话更心烦意乱,妈妈以切断经济补给作为要挟,逼迫着她回了东北。
2021年底统计,东北人口于10年内流失1101万人,其中黑龙江省减少了646万人,只有极少数会像朱姗姗这样被召回。
宋柯回想起来,汽车驶入东北平原的那个雾天,就是自己失去自由的日子
“在那儿你过的是什么日子,回家才能又更好的生活。”宋柯妈妈觉得只有自己身边,才是适合女儿生长的福地。
宋柯知道家里人想让她过什么样的生活,下岗是那代人的思想钢印,已经无法被抹除,万事求稳才是生活之道,即便他们一家没有被经济所困。
女孩儿,应该守家待地,有一份足够轻闲的正式工作,找一个有旱涝保收工作和社会地位兼具的男友,这才叫稳定下来。恋爱半年结婚,一年生孩子,到孩子三岁,家里掏钱给宋柯开个美甲店,权当消遣和补偿。至此生活就能像进了保险箱一样安全。
“30的人了在外面漂着,这不是长事。”
宋柯知道这不是长事,她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的是什么,这么漂着有没有意义。她只知道以上一切,都是她不想要的。
没成年的时候妥协于家里要求去读师范,上大学时候她就决定自己的路要自己选,没想到绕来绕去还是回到了原点。但如果让她来决定,她也说不出个打算。
当务之急,是要考下教师资格证,有份正式工作才有了在婚姻中谈判的底气。
2021年黑龙江报考中小学教师资格证的人有100496人,比起2020年增幅达27.5%,其中女性占比达82.5%,远超男性。这样看来,似乎“女孩应该守家待地”是种共同需求。
时不我待,她应该快快准备起来。
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唯一的活动就是窝在商业圈的教室里上课
宋柯没过过苦日子,但东北人早已经被下岗创伤后遗症沁入骨血,妈妈在亲戚朋友面前要强了一辈子也赢了一辈子,只输在一个“在家待着”的女儿身上。
这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词,之后亲戚朋友在问最近做什么,宋柯妈妈会用“在考教资准备当老师”作为应答。
在东北语境中,形容一个人“有正事”是最上等的褒义词,即便经常缺课落考不积极,宋柯还是会被评为“有正事”,和她一起旷课的发小也获得过这样的奖赏,发小被人问到的时候会回答“准备考研”。
宋柯在老家熬了半年,随时准备出逃又没有足够的勇气,直到亲戚介绍给她的对象照片实在让她看不下眼。
“我不是说以貌取人,但她真的觉得我就只配得上这样的吗?”
宋柯妈妈却说,接触接触没坏处,这男孩家庭条件不错,有正式工作也有小买卖,家里不就是不想让你吃苦吗?
宋柯听着“不想让你吃苦”后如同雷击,从杭州回东北之前听过一摸一样的话,向家庭妥协的第一次像是推到了多米诺骨牌,一次妥协事事妥协。
宋柯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出逃,这回无论谁说什么,自己都要离开东北。“求稳”的生活概念变成笑话,她觉得自己过去没吃过生活的苦,在老家的半年全部找上门。
爸妈态度强硬,再出走不会供给她一分钱,怒斥宋柯真的不如小时候懂事了。
宋柯说,妈,我快30了。
人生没有永远的安稳
东北,早年凭借工业基础,先迈一步成为共和国长子。从50年代开始兴建,哪个时期的东北人民切实过过一段好日子。
老一辈人始终觉得,生活只需要依靠工厂和国营企业单位,吃穿不愁,厂子和单位能保证自己的生老病死,也能让自己的下一代,下下一代都到老了有保障,人生进了保险箱。
国有企业改革将人们的美梦戳破,多批下岗的员工始终想不通,明明名字里有改革,为什么砸掉的是自己的饭碗。
“下岗”二字对经历过着一切的人来说都太残忍,千万人在短时间内失去工作,时代的悲歌像蝴蝶效应煽动、改变着无数个家庭的未来走向。
厂房废弃,烟囱熄灭,在这片土地人均拥有相近惨淡的人生。冰天雪地和苦难,让东北成为一片盛产幽默的土地,人们学会在逆境中保持乐观、自洽、勇往直前。
即便相隔二十余年失业的命运再次重演。
*本文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