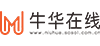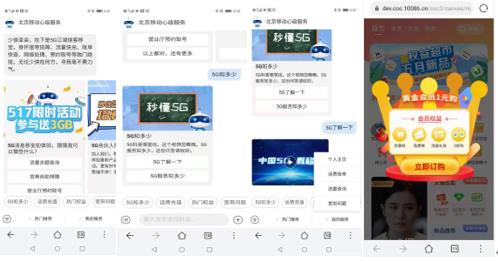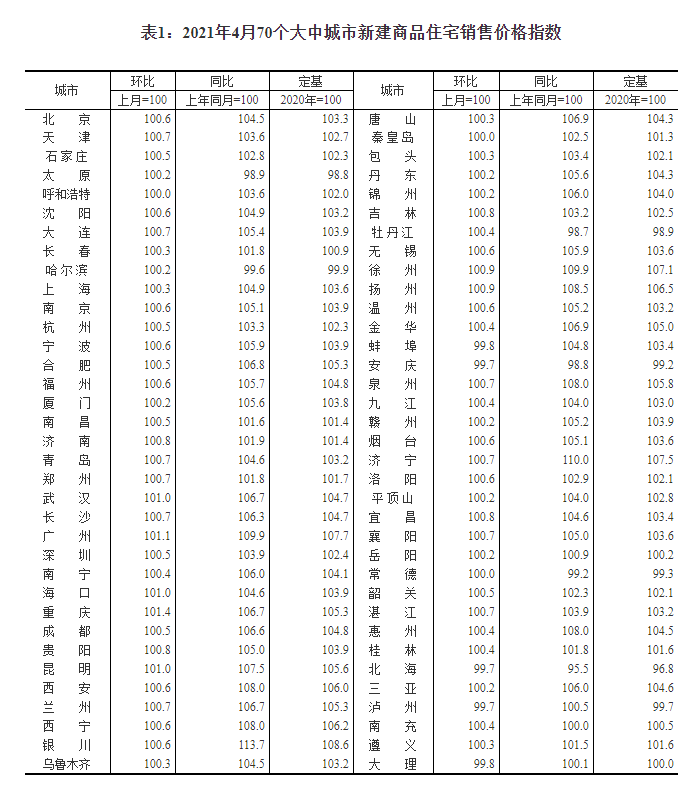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音乐先声,作者|Echo,编辑|范志辉
一部音乐传记片,却听不到主人公的音乐,会如何?
2020年上映的David Bowie最新传记片《星尘》,就是如此。这就像是一位有着先天缺陷的哑巴婴孩被要求演绎一场命定的音乐传奇,别扭且牵强。其原因,不知是不满意剧本还是价格没谈拢,导致没有获得歌曲授权。
最终,这部电影在豆瓣上的评分为3.7,票房也惨淡,堪堪6万美元。而Bowie的家人和歌迷一致认为,这部电影无聊且不准确。
那么,如果有了音乐版权和家属的合作,David Bowie的传记片会更好吗?5天前,BMG宣布将在今年发行第一部得到其遗产管理委员会正式授权的传记电影——《月球时代的白日梦》,并描述其将成为这位传奇人物的“权威新肖像”。
这部传记片聚焦于Bowie从1970 年代初期开始的职业生涯和音乐,借鉴了鲍伊的早期歌曲目录,包括《Changes》、《Starman》、《Ziggy Stardust》、《Fame》等,并“完全由鲍伊的旁白”指导,采用“前所未见的纪录镜头”。
据悉,BMG在2010年以1.86亿美元收购独立出版商Chrysalis后,就拥有了鲍伊歌曲目录25%的股份。所以,尽管华纳音乐最近收购了鲍伊的歌曲版权,但它与鲍伊音乐曲库的关系“不受影响”。
自Queen乐队的音乐传记片《波西米亚狂想曲》在2018年获得的成功,不仅好莱坞开始将音乐传记电影/传记纪录片看作新的金矿,音乐行业也开始重视这门有利唱片销量和版权价值的新生意。
音乐公司的新生意
除了这部即将在今年感恩节前上映的传记片, BMG在音乐电影领域早已经做了一系列尝试。
据音乐先声不完全统计,这家公司近几年已经参与制作了4部已上映的传记片/传记纪录片。而等待上映的,除了《月球时代的白日梦》,还有与Quickfire电影公司合拍的苏格兰音乐巨星Lewis Capaldi的处女作长篇纪录片。
与此同时,三大唱片和演出巨头等业内公司在这个领域也先后布局。
近5年音乐公司参与的音乐传记电影不完全统计
尽管David Bowie的传记片被BMG抢先一步,但手握众多音乐巨星版权的华纳音乐一直没有闲着。据悉,该公司其旗下的音乐娱乐部门是各种广受好评的音乐电视剧、电影和纪录片的幕后推手,比如获得艾美奖提名的音乐会电影《David Byrne:美国乌托邦》和音乐纪录片《劳雷尔峡谷:时光之地》。
早在2020年,华纳音乐就与奥斯卡获奖电影公司 Imagine Entertainment 签署了多年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制作和资助一系列以音乐为中心的影视项目,首次合作的《The Genius Of Aretha Franklin》传记剧集便获得了艾美奖提名。
紧接着,在2021年10月,华纳音乐又与国际影视内容公司SK Global宣布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宣称“这次合作将特别关注华纳音乐旗下众多著名的国际艺术家,尤其是在美国、亚洲和拉丁美洲”。
华纳音乐CEO史蒂夫·库珀对此评价道:“凭借全球的巨星人才名册和档案中丰富的音乐历史,我们有很好的机会通过传记片、纪录片和其他视觉的方式将音乐、叙事和人物形象结合起来。”一语点明了唱片公司涉足音乐传记电影的强大优势。
2020年,经过一场旷日持久的竞购战,索尼音乐获得了知名歌手Whitney Houston的音乐传记片《我想与人共舞》的制作权。据悉,该项目得到了相关遗产继承方和音乐制作人的支持,并由《波西米亚狂想曲》的编剧撰写剧本。此前,发行于2016年,改编自乡村音乐巨星Hank Williams自传的传记片《我看到了光》也有索尼音乐的授权合作。
而从2015年就进军纪录片的环球音乐,在2019年一口气发行了五部,其中就包括纪念帕瓦罗蒂逝世十周年的同名纪录片。2017年,环球音乐重组推出了专门负责电影、电视制作的宝丽金娱乐,使其不仅仅可以从音乐电影中收取授权费用,还能持续地获得分成。据悉,宝丽金娱乐不仅是2021年发行的纪录片《披头士:回归》的制作方之一,也是《天鹅绒金矿》的制片方。
三大唱片之外,演出巨头Live Nation也早已链接到了这一用视觉讲故事的商机。
2017年,Live Nation成立了电影和电视部门,为Lady Gaga和“吹牛老爹”Sean Combs制作了纪录片,并将其嵌入在巡回演出中;2018年,同样以Lady Gaga为原型的电影《一个明星的诞生》还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提名。不过,在新冠疫情刚爆发不久,该部门就因难抵影院关闭的经济压力而裁员。
如今,影院已经稳定开放,音乐行业在久久无法复苏的现场演出市场的空缺中,或许又将培育出音乐传记电影的肥沃土壤。从现有成果来看,音乐版权公司、唱片公司和演出公司,都有希望一展身手。
音乐公司为何纷纷押注传记片?
音乐类传记片似乎已经成为了电影、音乐两个市场共同的“香饽饽”。
2018年上映的《波西米亚狂想曲》让好莱坞开始把这音乐传记电影当作新的金矿。它以5200万美元的成本在美国本土轻松斩获2亿美元票房,位列2018年年度第六,全球票房近9亿美元,不仅创下了影史最高的传记片票房纪录,而且拿下了4项奥斯卡大奖。紧随其后,北美影院在2019上映了10余部音乐传记电影。
显然,在一个原创电影不断被超级英雄和无限续集湮没的好莱坞电影时代,音乐传记片为观众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和更具文化意涵、历史感的故事。
对于音乐公司而言,在一个实体专辑销量萎缩、演出陷入停滞的后疫情时代,他们也有了更多动力来尝试这类项目。传记电影不仅能充分挖掘音乐版权的价值,而且有助于促进音乐人的唱片销售和版税收入。
数据显示,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上映后,《皇后乐队精选集》很快就重返iTunes官方专辑排行榜第一名,并在2019年成为其有史以来第一张销量达到600万的专辑。同时,唱片时代的巨星也通过电影获得了跨时代的收益——广泛的流媒体播放带来的巨额版税。财报显示,皇后乐队在2020财年共产生了4195万英镑收入,其中版税收入4167万英镑。
即使不拍传记片,仅凭对某一音乐巨星的致敬、融梗,并取得一两首原型人物的歌曲版权,或许也能如法炮制一场票房狂欢。
于是,音乐公司们也纷纷将音乐授权给非音乐传记片电影。例如2019年上映的《光盲青春》,讲述的是一个英国少年发现了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音乐,同年的《昨日奇迹》则想象了一个没有人记得披头士的世界——除了想成为创作歌手的主角。
上映时,二者都不约而同地带上了喜剧类电影的标签,获得了不超过7的豆瓣评分。但后者仍取得了超过1.5亿美元的全球票房,前者票房则不足2000万,主要原因或许可归结为原型人物影响力的差异。
诚然,音乐传记电影的拍摄,电影公司和音乐公司都有着自身的利益盘算。但对于音乐人而言,动机则更为纯粹,这是叙述自身故事、塑造他们如何被记住的重要机会。
对于拍摄中的关于自己的纪录片,凭借热门歌曲《Someone You Loved》走红的Lewis Capaldi在采访中表示:“当我的工作多年来像一堆燃烧的垃圾一样被接受,我很兴奋能永久记录我的梦想。”
而对于“过时”的音乐人而言,在信息过载的时代,几十年前的音乐可能会默默无闻,传记电影则可以将经典音乐重新介绍给年轻的听众。
“老一代音乐人没有从流媒体中赚钱,同时已经好几年不能像以前那样巡演了,他们以往习惯的收入来源也已经枯竭”,《滚石》杂志资深作家大卫·布朗说,“如何让他们的音乐在公众视野中出现以维持生计?传记片和音乐剧是值得一试的路子。”
去年年底,在接受《洛杉矶商业日报》采访时,迈克尔杰克逊的遗产管理人约翰布兰卡表示,除了刚刚开演就场场售罄且备受好评的音乐剧《MJ》外,他们正在开发的迈克尔杰克逊传记电影。
总之,已经获得成功的乐队和音乐人,无论其走红周期长短,似乎都有一个惊人的故事要讲述,但要讲好他们的故事并不容易。而音乐传记电影这门生意,也没有看起来那么好做。
音乐传记片这门生意好做吗?
在欧美电影界,音乐传记片有丰富的历史。
上世纪50、60 年代,诞生了关于猫王的30多部电影,关于披头士乐队的3部电影,其中《黄色潜水艇》不仅收获了近130万美元的全球票房,还获得了8.9的豆瓣高分;70年代,据乡村歌手洛蕾塔·林恩的生活改编的《矿工之女》获得奥斯卡提名;到了80年代,暴力和悲剧色彩一度浸染传记电影,如性手枪乐队的《席德和南希》、《爱与爱有什么关系》。
可以看到,音乐传记片从来都不短缺,但千禧年的交替带来了一些标准化的电影,这些电影被复制、模仿,然后变成音乐人的武器。
2002年,知名说唱歌手Eminem利用自己在音乐上的成功拍摄了一部基于自己真实生活改编的电影《8英里》,在说唱界获得了广泛赞誉。2004年到2007年,音乐传记电影滑向模式化,它始于一部关于Ray Charles生活的电影《灵魂歌王》;紧随其后的是追溯John Cash成名历程的《与歌同行》,全球票房收入超过1.8亿美元;然后是对它们进行模仿的《永不止步:戴维·寇克斯的故事》,还获得了第65届金球奖。
回看国内,音乐传记电影寥寥,且以主旋律作品居多。去年的《梅艳芳》不仅口碑一般,还引发了名人商标纠纷;2019年的洗星海传记电影《音乐家》则十分冷门,没有引起大范围讨论。再往前追溯,就只能想到1999年的《国歌》。
如此看来,音乐传记电影方面欧美远远领先,但其成功也仅仅停留在商业层面。在艺术层面,真实还原和戏剧性表达间的冲突,商业推手下的公式化创作,都大大压缩了音乐传记电影的探索空间。
即使是《波西米亚狂想曲》这部有史以来票房最高的音乐传记片,它在烂番茄上仍只获得了60%的“新鲜”评价,还达不到最低要求75%的新鲜标识。在流行的评论网站Metacritic上也只获得了49分。评论家们认为,它不仅有许多历史错误,在叙事上也无可避免地落入了传记片的流水账窠臼。
关于音乐传记电影的拍摄难题,除了表达,更基础也是更关键的是版权难题。
除了前述提到的《星尘》没有得到David Bowie的任何一首音乐版权授权,以Jimi Hendrix(被公认为摇滚史上最伟大的电吉他演奏者)为原型的传记片《与我同行》同样没能取得其遗产管理委员会的音乐授权。
关于已故名人的传记电影,遗产管理委员会的授权始终是一大关键。而即使人物原型在世,仍然存在一些潜在甚至未知的困难。
比如1998 年发行的《天鹅绒金矿》,因为最初的剧本对David Bowie的生活刻画过于细致而让他大为不满,甚至考虑起诉制片人,直到他们达成协议重新编写这部电影,而且Bowie否决了他的歌曲出现在电影中的提议。但这部电影仍凭借它对那段无可复制的华丽摇滚时代的唯美刻画和对鲍伊歌曲的重新演绎,被誉为“终极版的大卫·鲍伊传记片”。
可以看到,音乐传记电影凭借其原型的广泛影响力,往往站在相较其他类型片更高的起点上,同时也面临更多的困难。但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它的火热无疑提供了一种将音乐与影像结合营销的新思路。
去年,环球音乐推出了专注视觉表达的水星工作室,不仅将音乐作为电影素材,将音乐表演现场作为珍贵的影像材料进行重制、修复或脚本化创作。最近,它还制作了Apple TV+纪录片《1971:音乐改变一切的那一年》。这部纪录片用8集记录了在1971年里发生的众多文化事件,比如音乐与种族、民权斗争的关系,以及毒品文化的影响。
毫无疑问,纪录影像和音乐版权的资源优势,无疑是当下唱片公司相较于流媒体的最大优势。而一部成功的音乐传记片,在帮助音乐人获得商业成功的同时,也让后来者得以领略他们光鲜背后的隐秘与伟大。